-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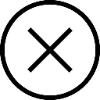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更是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本版关注“新质生产力”,摘编专家观点,探讨如何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当前,全球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世界大国争夺科技制高点的竞争日趋白热化。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表示,对于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关键期的中国而言,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既是应对时代变革的战略选择,也是中国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近年来,中国科技创新发展非常迅猛,研究与试验发展(R&D)投入连续7年都保持两位数增长,远高于GDP增速;2023年R&D投入强度达到2.64%,超过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科技由此取得了一系列战略性成果,比如高端芯片虽然遭到了外部“卡脖子”,但还是取得了进展,重型燃气轮机、商业大客机、大型游轮等领域也接连实现重大技术突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对中国的排名,2022年是第11位,2023年是第12位。在世界排名前30位的经济体中,中国是唯一的新兴市场经济体。
“但是我们也有短板弱项,主要表现是原创能力不强、原创成果偏少,这主要受制于基础研究相对薄弱。”王一鸣说,“过去可以购买其他国家的科技成果,但是现在外部环境变了,不可能重复过去的模式。”过去中国R&D的比重一直比较低,2020年占GDP的比重仅为6.32%,而OECD国家平均水平为15%~25%,基础研究是中国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导致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王一鸣表示,对此,中国要从过去的跟随性创新模式转向在部分领域引领性创新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再通过适应性改造和再创新,来缩小自身产业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这个过程也被称为“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过去依靠这种模式取得了很大成功,成功之处在终端产品领域,比如百万千瓦级超超临界发电机组、高铁成套设备和技术、5G通信设备等均具备国际竞争力。但是,承载关键核心技术的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华体官方网页版软件等这些中间品,仍面临被“卡脖子”的风险。所以中国必须转向在这些领域引领性创新,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改变不了被“卡脖子”的被动局面。
新能源华体(中国)的异军突起,说明中国在部分领域完全可以实现领先。“以前是市场换技术,以后要技术换技术,甚至拿技术换市场,这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关键。”王一鸣说。想实现这种突破,要从过去的集成创新转向原始创新,而转向原始创新需要加强前瞻性的基础研究,通过基础研究来实现带动更多引领性的原创成果和战略性技术的突破。
王一鸣表示,只有创新但不能转化为产业化成果,也解决不了问题。“我们既要有从0到1的原创,从1到10的应用研究,也要有从10到100的科技成果转化,从100到N的大规模产业化。”王一鸣说。从概念设计、技术研发到中试再到产品,需要全链条的创新。当然,发展新兴产业绝不是要放弃传统产业,传统产业是中国实体经济的基本盘。如何提升传统产业,则要靠数字化转型、智能化改造。 (文章摘自:《紫荆论坛》)
新闻附件: